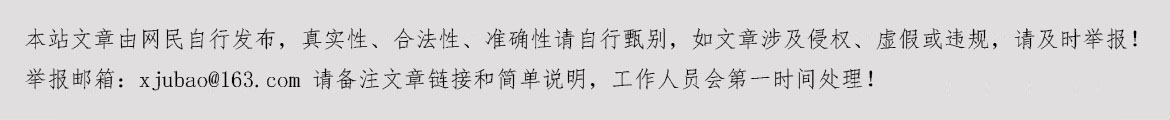德姆拉山上的三天两夜
冯正荣
1982年2月24日《解放军报》头版的醒目标题是“搏击风雪八昼夜”,副标题是“记成都部队某部汽车兵的事迹”。长篇通讯是这样描述的:今年元旦前的十多天,一场特大暴风雪袭击了西藏高原,寒风怒号,飞雪扑面,千山万壑雪海茫茫,电线成了碗口粗的冰绳,参天大树挺不住风吹雪压,歪倒在三尺深的雪地上,暴风雪以它不可阻挡之势,向着正在飞驰在川藏线上的三个汽车部队袭来,两千三百多名干部战士面临着严峻的考验。
1982年2月24日的《解放军报》
当年我们连队被暴风雪堵在德姆拉山上三天两夜,这就是“搏击风雪八昼夜”的组成部分。1981年12月,我在汽车第十八团十三连担任指导员,带领车队到西藏察隅边防部队运送过年物资,车队到然乌朝左手边分路上了德姆拉山。德姆拉山海拔4900多米,山上植被少,空气稀薄,加之这是川藏线的支线,道路修得不怎么好,弯多坡陡,稍不留神就会出现车毁人亡的事故。我们每次翻越德姆拉山都能在路边上看到翻了车的汽车残骸,非常恐怖。当地流传的一句话叫:天不怕,地不怕,就怕翻越德姆拉。德姆拉山是到察隅边防的一道“鬼门关”。那天,我们还没有到山顶,山上已经开始下雪,当时我就预感,这趟跑察隅情况不妙。
我们到边防团下货后,按常规休息一天,恢复车况,恢复体力。我们知道德姆拉山下雪后行车困难。于是,下货后的当天下午就返回到了德姆拉山下的古井兵站,到兵站的时候雪已经下的很大了。在兵站住了一个晚上,早晨起来一看,兵站的雪已经很厚了,山上的雪可想而知。我们分析,今天翻过德姆拉山已经不可能了。我们和兵站的领导商量,给我们退一餐伙,兵站事务长算了一下,给我们退了半袋面粉,几个红烧肉罐头。
作者冯正荣(后排左二),文中出现的班长顾寿(后排左一)
就这样,我们要求每台车挂上防滑链条就出发了。雪越下越大,没行驶多远,不断有车辆打滑。为了保证安全,遇到打滑的车辆就动员大家往轮胎下面撒沙子,垫树枝,一台车一台车往前挪动。整整行驶了一天,才走了三十多公里。
天渐渐黑了,再行驶就不能保证安全了。于是,我们决定就地休息。大家饿了一天了,在古井兵站退了一餐的面粉和红烧肉罐头给各班分了一半。大家从山上找来树枝,支上几块石头,用洗脸盆当锅(那个年代的洗脸盆都是搪瓷的,可以烧),山上没有水,就把雪烧化当水。山上的雪看上去很白的,烧化了,里面有树叶,有沙子,还有牛粪末,实际上很脏的。在荒无人烟的雪山上,没办法啊!只有用这种水煮面糊糊让大家充饥。有的战士风趣地说,山上没调料,树叶子、牛粪末就是调料啊!我们的战士在这种艰难困苦的环境里,还是充满着乐观主义精神。
当天晚上,大家都坐在驾驶室睡觉。我们要求每过两三个小时,就要发动一次车,以免冻坏发动机。再就是坐在驾驶室可以互相照应,防止在高山缺氧的情况下,有高山反应的战士睡着了醒不来。我作为带队干部,尽管提了要求,心里还是不踏实,万一那台车的驾驶员睡着了,没及时发动车,发动机冻坏了,不仅这台车走不了,后面所有的车都走不了。万一那个战士睡着了,出现了高山反应,在驾驶室缺氧的情况下,可能就永远睡着了。我想到在德姆拉山上过夜,是人命关天的大事。于是,我把裤腿用绳子捆在毛皮鞋上,以防雪钻进毛皮鞋里面。我坐的63号车驾驶员姬玉明(1978年入伍的山西省永济县人)跟着我,拿着手电筒,踩着膝盖深的积雪,每过两三个小时就一台车一台车地喊大家发动车。当我检查到51号车的时候,看到班长汪均明(1971年入伍的四川省仁寿县人)把学员孙洪虎(1979年入伍的四川省古蔺县人)抱在怀里,不停地往学员嘴上淋水。当时学员孙洪虎出现了高山反应,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雪山上,没有吸氧设备,也不可能送医院。就这样,汪班长用自己的胸膛温暖着战友,熬过了一个难熬的夜晚。
文中出现的教歌员吴永新
我在这个晚上只打了几次盹,天快亮的时候,为了给大家提提精神,我学起了公鸡叫,大家在荒无人烟的雪山上听到公鸡叫很奇怪,纷纷从驾驶室伸出头来张望。后来才知道是指导员学的鸡叫。在这种情况下,还是要想办法生存,想办法战胜困难。
第二天,我继续组织车队前行,好不容易到了山顶,一台地方车滑沟,把路堵死了。我们连队的干部战士把滑沟的地方车推上了公路,车辆慢慢向前挪动,没走多远,前面的车辆又不动了,我走到前面一看,道路完全堵死了,没有一点松动的迹象,看来今天又在雪山上过夜了。
这一天虽然雪不下了,大家坐在驾驶室里还是又疲倦、又饥饿、又着急。怎么办呢?我找来排长孙存万(1972年入伍的甘肃省民勤县人),我说,你是连队演唱组的组长,我们连队在重大活动都要召开联欢会,今天我们就组织一个雪山联欢会吧!说干就干,孙排长吹哨子把大家集合起来了,大家坐在雪地上,联欢会开始了。说是联欢会,实际上就是逗逗乐。有的表演一个小节目,有的讲个故事,有的谈点人生感悟。我们连队有个战士叫吴永新(1975年入伍的广东省信宜县人),他说,我老家在广东湛江,当兵前经常看到的是大海,没有看到过下雪,那时候想,看到美丽的雪景多好啊!现在看到雪是这么多恶劣,我想家了,我想家了…说着说着就流下了眼泪……我说,吴永新,你是连队教歌员,指挥大家唱歌吧!吴永新一听指挥唱歌,一下来了精神,大家在雪山上唱起了《团结就是力量》、《过雪山草地》、《战友之歌》等等。大家越唱越有劲,唱完歌继续挖雪开路。这一天只向前挪了几公里。前一天剩下吃半餐的面粉,分到各班,一整天大家就吃了一点面糊糊充饥。
天黑了,我还是要在车队前后来回喊驾驶员发动车,我每次喊大家发动车,带队车驾驶员姬玉明都拿着手电筒跟着我,我看到他也很累了,我说,这次喊大家发动车你就不去了,他说,指导员向全连负责,我要向指导员负责,晚上天黑,指导员摔着了怎么办!我说你休息一下,明天还要开车。他说,这一路过来,危险路段都是指导员开的,你明天也要开车的。我说服不了他,他还是跟着我,一晚上跑了三四趟。这个战士给留下的印象太深了。当时我们开的解放牌汽车,车况不太好,一路行车,一路修理,冬天天气冷,他的手上全都裂了口子。当时部队发的线织的白色劳保手套,他戴的手套都染成红色了,晚上手套和手粘到一起取不下来,我给他淋上水才慢慢脱下来。多么可爱的战士啊!2018年,我当指导员时期的战友在四川雅安市举行联欢会,本文中提到的排长孙存万、班长汪均明、顾寿、教歌员吴永新都要来。我想姬玉明一定会来的。结果找战友通知他的时候,听说他退伍回地方后因病去世了……当我得知这个消息后,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……我常常想起他的样子,高高的个子,瘦瘦的,见到人面带笑容……我常常想起那双带血的手套……
作者冯正荣(左二),文中出现的班长汪军明(右一)
等到天亮了,担任救济车的班长顾寿(1972年入伍的甘肃省武威市人)报告,救济车上的压缩饼干每个班只能分两块。压缩饼干分到各班后,谁也不肯吃,我提议每人咬一口充饥。战士们说,指导员你先咬,我说,好!我先咬一口。我摆出一副大口咬的样子,嘴张的很大,实际上只是舔了一下。就这样,一块压缩饼干传了一圈,谁也不肯咬一口……我们部队就是这样,越是困难的时候,大家的风格越高尚,越能表现出官兵的团结友爱。
这一天大家忍饥挨饿,前面车一动,我们赶快跟着移动,车辆开始下山了。在冰雪路上行驶,上山容易打滑,下山情况好得多。在黑夜中我们已经看到然乌湖了。当晚十点多,我看到最后一台车开进了然乌兵站,我坐到饭堂的板凳上站不起来了。也许是太累了;也许是看到全连一台车没少,都到兵站了;也许是看到全连官兵一个个面容憔悴,心里难过了……
全连官兵三天两夜没吃饭,当晚在然乌兵站吃了一顿热饭。这三天两夜全连官兵经历了苦与难、生与死的考验。事实证明,只要官兵团结一致,什么艰难困苦都能战胜。
德姆拉山过来了,冰雪路仍然在前面考验着我们。从然乌兵站继续东返途中,然乌沟、安久拉山、怒江山、东达上、宗拉山一路都是冰雪,我们的车队走走停停,加上德姆拉山上的三天两夜,在崎岖危险的山路上行驶八昼夜,未出一起事故,未伤亡一人,暴风雪被我们战胜了,我们创造了奇迹。
作者冯正荣(前排左一),文中出现的排长孙存万(后排右一)
(注:本文插图均由作者提供)
作者简介:
冯正荣甘肃省酒泉市人,1954年2月出生,1972年12月入伍,入伍后就成了川藏线上的一名汽车兵。曾任连队文书,营部书记,连队副指导员,指导员,副教导员,宣传股长,兵站站长,宣传科长,大站政委,干休所政委。2003年在部队退休后,一直在川藏兵站部机关帮助到2021年。